今年夏天,四川省凉山籍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毕业生苏正民因6000字毕业论文致谢“火了”。这个九月,他回到家乡,成为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第二中学的支教老师。
人们透过“致谢”热议苏正民的成长与过去,但在“出身贫寒”“致谢感恩”这些别人概括的关键词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样一路走来?他被谁影响?又被什么改变?中国之声对话苏正民,聊聊他走过的路。

新学期,支教教师苏正民在凉山越西县第二中学课堂上,他教初一年级“道德与法治”课,带三个班。(受访者供图)
父母撑起童年世界
支教老师为少年打开窗
记者:两万五千多字的论文当中有将近四分之一是感谢,这个致谢我听说你写了两个晚上?
苏正民:对……你说真正要感谢的话,我幸运,幸运在哪?就幸运在遇到了这么多好心人士,这么多贵人相助,我能够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能够走出大山,不再重复父辈们的道路,一直到今天能够为孩子们去做点儿事情。
苏正民用“幸运”和“贵人相助”概括自己的经历,他年幼时,最重要的人是爸爸妈妈和支教老师。

右一是爸爸,右二是妈妈抱着苏正民,前排最小的是姐姐(受访者供图)
记者:你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苏正民:很难形容。可能一想到父亲,首先想到的他是一个坚信读书和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一个人,在当年的情景下是很难得的。把我们三个从小都送进学校,一直到自己生病了,依旧不愿意放弃。他是一个特别老实特别忠厚的人,只要别人叫他帮忙,他都会去帮,他是特别能够吃苦耐劳的一个人。
记者:妈妈在家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苏正民:妈妈虽然没读过书,但是她讲的很多话,我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朴实很有道理的,就像她经常告诉我们“别人给你一碗米,你要回馈别人一袋米”等等。

苏正民和妈妈、妹妹在参加活动(受访者供图)
小时候,因为亲戚们开玩笑说家里的“独儿子”以后独享家中财富,苏正民会偷偷去看家里存折,每次都能看到几百或几千的增加,“感觉爸爸和妈妈撑起了整个世界”。
童年的世界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沙马拉达乡的小山村,从沙马拉达通往外界,有成昆铁路;苏正民通向外界的窗,是支教老师。
苏正民:支教老师不会说彝语,她听不懂我们说的,我们也听不懂她说的,老师就重复重复再重复……
记者:他们(支教老师)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苏正民:我觉得首先是让我听懂了汉语,让我能够识得一点儿字。其次是这群人给我留下了一辈子难以磨灭掉的一些印记……他们是我最终选择回到家乡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最早的一个种子。它种下了,也生根了、发芽了,不知道能不能开花结果。
年少坎坷
“张妈妈”成为灰暗人生的一束光
记者:在你中学阶段其实是经济上压力最大的。
苏正民:上了初中之后,吃饭的时候,我们打一个素菜,隔几顿打一个荤菜,但是别人可以打两三个荤菜和两三个素菜……当时的情感很复杂,但是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自卑,觉得跟同学们差距很大,跟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很孤独,成绩也不是很好。初一寒假回家收拾好我的小行囊,就想去打工了。
爸爸请我吃了一顿“竹笋炒腊肉”,用我们四川(话来讲),狠狠揍了我一顿……
苏正民回到学校埋头学习,学习上有了起色不多久,初二那年,积劳成疾的爸爸罹患心脏病、肝囊肿、肺水肿去世,治病花光了家中积蓄……苏正民辍学了。
苏正民:爸爸去世之后家里面就欠下很多钱。
记者:欠下多少钱?
苏正民:当时应该是有十多万接近二十万。每个星期五,六十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了,得去找邻居去借。就觉得很困难,不想给妈妈再添加负担了,觉得妹妹更聪明,把希望留给妹妹。
记者:这个过程当中我挺难想象当时的心理斗争的,你不纠结吗?
苏正民:没有选择了。
一个多月后,苏正民遇到了“张妈妈”。
“张妈妈”名叫张俊兰,是《天津日报》记者,从1997年开始,她三十多次走进凉山,她的“张俊兰工作室”先后帮助了几万个大凉山的孩子,苏正民辍学之后正是得到了她的资助。苏正民在论文致谢里写,“那时的我,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直到一个人像一束光一样照进了我灰暗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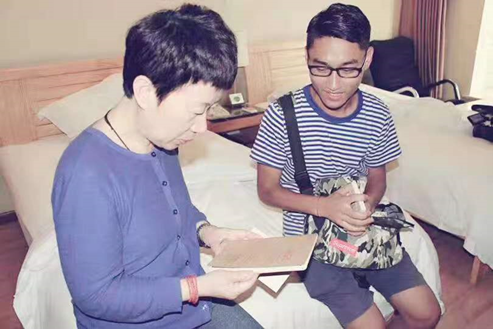
张俊兰到凉山开展资助,读高中的苏正民看望“张妈妈”(受访者供图)
苏正民:当时班主任知道我的情况很揪心,然后就找《天津日报》的张俊兰记者,给我提供助学金,然后也为我申请到了学校的国家助学金,村里面也在帮我们家申请低保。因为我心里面还是想回去,我不想一辈子都是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十多岁二十多岁早早地就结婚生子,然后照顾孩子,过完自己的一生。
记者: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张妈妈真正见面接触是什么时候?
苏正民:高一的时候,她到我们学校来,把助学金亲自装在信封里,发给在我们学校每一个受她资助的学生……在没有见到她之前,觉得她是那种很“高大上”的人。但是跟她见面的时候才发现,她跟自己母亲一样很朴实:剪了一头短发,个子也不是很高,说话也特别温柔,握着我们的手。
很多年后苏正民才知道,那时,张俊兰每次坐40小时火车才能到凉山。
求学向上
“不能将自己的心也锁在层层叠叠的峦障中”
2017年,苏正民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学少数民族预科班,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当时的“211大学”的。可苏正民并没能一下子跟上大学的节奏,他说自己“依旧拒绝同学们的热情对待,对老师朋友的关心下意识疏离”。
直到大一下学期,老师推荐他参加湖北省“百生讲坛”演讲比赛。苏正民动心了,他觉得,“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不能将自己的心也锁在层层叠叠的峦障中”。

“百生讲坛”上台前的苏正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供图)
苏正民:因为这件事就给了自己很大信心。我就想,只要自己努力,依旧是能够和其他同学一样,甚至能够比其他同学做得更好。因为有自信了,愿意去跟别人打交道,愿意去主动接触这个世界、接触其他东西,我觉得肯定是很不一样的。
记者:我们今天聊的过程当中,我已经记不清你有多少次讲到自信这件事了,自信你觉得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自信有多重要呢?
苏正民:怎么说……它是一种态度和一种理念,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每一件小事到大事,可能明显或不明显。至少我觉得大学四年下来,如果我依旧保持着最开始的状态,我可能无法做助学计划,无法做专项基金,无法做服务队。
有很多凉山的孩子就是这样,人是走出了大山,心依旧没走出大山……(自信的人)他能够获得的成长、获得的资源、获得的机会肯定会比内向的人多得多,无论于公于私,我觉得自信都会是一件好事。

暑假,苏正民连续操持到第三年的夏令营上,他请来的志愿者和山区学生在互动
毅然回乡
“因为我见过更有意义的事情”
支教一年后,苏正民将回到学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未来,他选择“回到家乡,回到大凉山”。多坐几年冷板凳,多多磨炼自己,是苏正民的希望。

苏正民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发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供图)
记者:你什么时候觉得“我要回来”?
苏正民:刚上大学的时候有回来的想法,但是不坚定,觉得回来也行,留在大城市也挺好。跟着基金会做了很多事情,接触到很多小孩,就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首先,对我个人来说,我很快乐,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实现了自己的一点点价值。然后觉得这边可能也确实需要(我这样的人),因为有很多人从千里之外来到这里帮忙,在这里做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建设自己的家乡,谁又来建设家乡呢?一个人立自己的志向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你一旦立下来,你可能未来就会一直朝着这个方向靠近,即使成为不了,你也会离它越来越近。

暑假,苏正民在西昌组织志愿者培训
关于自己选的前路,年轻的苏正民也有担心,比如难以汲取大山外面更多的东西、可能不会富有……但他清楚:“没有一条路是十全十美的。”
苏正民:“房子能住就行,日子能吃就行”,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可能更合适。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见过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不是指它(赚钱)没有意义,而是我见过更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这个选择对你来说两难吗?
苏正民:当你提到父母的时候,我觉得这确实是个两难的事情。但是在大家和小家之间,如果非有一个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大家,因为这样我会更快乐。
有网友说,“十年后再看,希望他能保持初心服务人民。”
苏正民:只有说真正到自己生命停止的那一天,依旧能够不忘初心,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不忘初心,我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十年这么简单,是希望自己到人生终结的那一天,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

苏正民(右)和总台记者王娴在志愿者活动上
原文链接: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share_to=wechat&item_id=2839073708520605425&track_id=926A92A2-4FAD-48C8-9689-B76A40A65646_683601919026
